世俱杯火爆!5.5 万观众见证博卡青年 2-2 本菲卡,4.5 万蓝白狂潮席卷迈阿密
北京时间 6 月 17 日,2025 年国际足联世俱杯小组赛首轮在迈阿密硬石体育场展开焦点战,阿根廷豪门博卡青年与葡萄牙劲旅本菲卡以 2-2 握手言和,55574 名现场观众共同见证了这场充满戏剧性的对决。其中博卡青年球迷占据压倒性优势,超过 4.5 万人身着蓝白球衣组成 “海洋”,为本队呐喊助威,而本菲卡球迷仅约 1 万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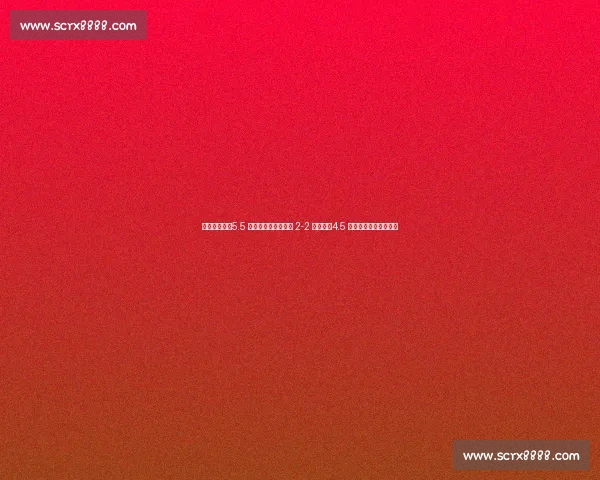
比赛跌宕起伏:红牌、点球与救赎
比赛开场后,博卡青年迅速掌控局面。第 21 分钟,布兰科边路穿裆突破横传,梅伦蒂尔小角度推射破门;第 27 分钟,埃尔顿・科斯塔头球摆渡,巴塔利亚头球扩大比分至 2-0。然而,本菲卡凭借两位前阿根廷国脚的出色发挥实现绝地反击 —— 迪马利亚在半场补时阶段主罚点球命中,奥塔门迪则在下半场用一记教科书般的头球将比分扳平。值得一提的是,迪马利亚此役是其职业生涯告别战,他用进球为自己的传奇生涯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比赛中裁判的判罚成为焦点,全场共出示三张红牌:博卡替补席上的埃雷拉因抗议判罚被直接罚下,本菲卡的贝洛蒂和菲加尔也因过激动作染红离场。这种高强度对抗让比赛一度陷入混乱,却也将南美足球的野性与欧洲球队的严谨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必一运动,bsports必一登录入口,bsports必一体育,bsports官网世俱杯热度标杆:上座率超 85%
硬石体育场可容纳 65000 人,本场比赛上座率超过 85%,是本届世俱杯首轮观众人数第二高的场次,仅次于巴黎圣日耳曼对阵马德里竞技的 80619 人。值得注意的是,博卡青年的球迷群体展现出惊人的号召力,他们的助威声浪几乎贯穿全场,甚至让中立球迷感叹 “仿佛置身博卡糖果盒主场”。
足坛名宿云集:卡瓦尼、巴乔见证经典
本场比赛吸引了众多足坛名宿到场观战。博卡青年前锋卡瓦尼因伤坐在看台,而巴乔、里克尔梅等传奇球星也现身观众席,共同感受这场跨越洲际的足球盛宴。正如《中国青年报》所言,两队虽近年战绩有所下滑,但其 “融入血脉的足球基因” 仍能唤起球迷最纯粹的热爱。
这场平局让两队同积 1 分,后续将争夺晋级淘汰赛的资格。对于博卡青年而言,球迷的狂热支持是他们继续前行的动力;而本菲卡则需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调整状态,避免重蹈 “先丢两球” 的覆辙。世俱杯的舞台从不缺乏惊喜,这场充满戏剧性的对决,无疑为全球球迷留下了深刻的记忆。